·南方周末
近期,一场关于“大厂同年”的争论,引发广泛关注。某互联网大厂中层管理人员在进入企业后的培训中,结识了目前团队中的大部分成员。他们在培训中得以相识相知,清楚各自的潜力和能力,进而组成团队共同打拼。
一部分网民认为,这种利益共同体是高效的工作团队。另一部分网民则认为,这种由“同年”“同门”关系而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天然具有争权夺利、山头主义的特性,是拉帮结伙的职场毒瘤。
其实在历史上,这种由“同年”“同门”组成的利益共同体,也是一种相当悠久的传统,能带给我们相当多的启示。
在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恢复科举制度的目的之一,是打击朋党政治,但他忽略了科举制度本身也是抱团搭伙的温床。既然科举是跻身新贵的唯一途径,“新贵”和“预备新贵”也就自然而然将科举作为彼此识别、认同和联系的集体意识。“士大夫”集团就此产生。
在集团内部,士大夫又可以根据各自的出身、地域、所代表的地方势力抱团,结成更小的利益集团。在这个共同体之中,个体因利而聚,利尽则散,彼此之间的一致性只在关乎共同利益时才显现。
但在先秦时期,这是为儒家所不齿的行为,但明代的士大夫自有办法处理这种冲突。因为明朝的乡试、会试两级考试都是以治理区划为单位举行的,因此地域成为抱团的天然纽带。在考试中获得功名的士子,往往将主持考试的考官拜为老师,而对同乡同年同科者,均以同门相称。而对同一“师门”但同乡异年同科者,则以师兄弟相称。这样,在“神圣”的师生关系掩盖下,一种利益共同体的雏形就形成了。
《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后,张乡绅前来与他攀附时说:“适才看见题名录,贵房师高要县汤公,就是先祖的门生,我和你是亲切的世弟兄。”房师是主持乡试的考官,和范进并没有实际上的教学关系。在范进中举之前,张乡绅是绝不会主动结交范进的。而在范进中举之后,立刻就能用这种“师门”关系与范进攀上关系,范进也对此表示了认可。
利玛窦在描述这种关系时写道:“在这样考取学位(科举)的过程中,确实有某些值得称道的东西,那就是在同年的候选人之间发展起来的关系。那些在争取更高学位当中被命运带到了一起的人们,在此后的一生中都彼此以兄弟相待。他们之间相互有着和谐和同情,以各种可能的方法互相帮助,甚至惠及亲属。”
利玛窦显然未能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同门之谊”远远不止“惠及亲属”这个程度。他们在未成为官员时,彼此以师门结为师兄弟,在获得功名之后,则结成利益同盟,争权夺利。相比之下,清朝顺治皇帝显然对明代士大夫们的门道认识得更为透彻,他在解决明代遗祸蔓延至清初的问题时,首先就从源头上禁止士大夫彼此以师门结交攀附,他说:
“今观风俗日移,人心习于浇薄,遇幼年受(授)业之师,略不致礼,惟以考试官为师,终身加敬。夫以理论,则自幼教育之师,受其诲导,自宜始终敬礼;若考试官员,朕所遣也,岂受(授)业者比哉!自后此等悉直明示禁革之!”
大意是,士子道德败坏,见到真正对自己有传道授业之恩的启蒙教师礼节有亏,反而对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尊敬有加,终身奉为恩师。按理来说,士子的启蒙和授业老师才是最应该受到尊敬的,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不过是皇帝派遣的官员,怎么能和授业老师相比,以后不准士子再拜主考官为师。
然而,利益目标和实现途径一旦固定且唯一化,人类结成共同体追求利益的天性就无法压制。即使清代吸取了明亡的教训,采取了严厉的压制措施。但这种压制措施解决不了科举制度与人性中天然趋利的部分结合之问题。最迟不过至乾隆中后期,拜师门习气又在清代科场流行起来,贵族、官员亦沉沦其中不能自拔。清朝亦步了明朝的后尘,在晚期为此所困。
可见,在社会中,作为个体的人出于实现个人目标的目的,与其他个体结成利益集团,即所谓的“抱团”是人类天性,是任何强制手段也无法消除的自然现象。而至于个体“抱团”是有利于还是有害于特定的组织机构或社会,则是由激励机制和价值导向所决定的。即使受此荼毒最为深刻的明朝,由张居正和他的湖广同乡组成抱团推动“张居正改革”,成功挽救了摇摇欲坠的明王朝并使其延续到了十七世纪,被称为“暮日耀光”。
(作者系大学老师、历史学者)
•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刘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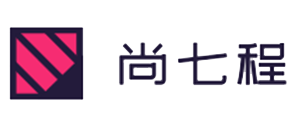

评论